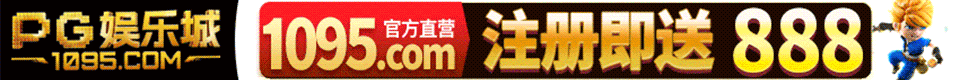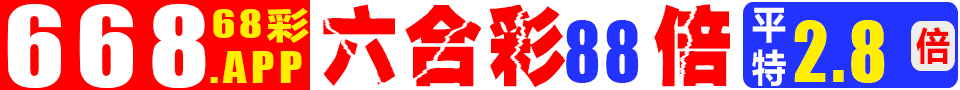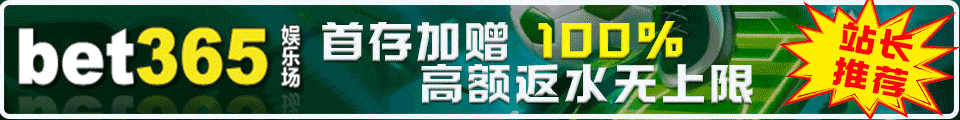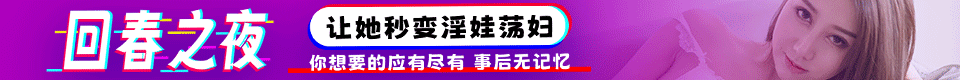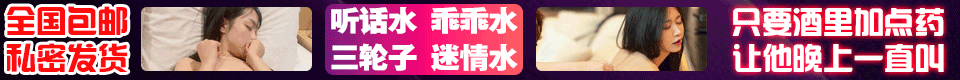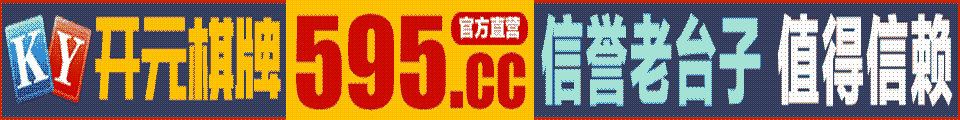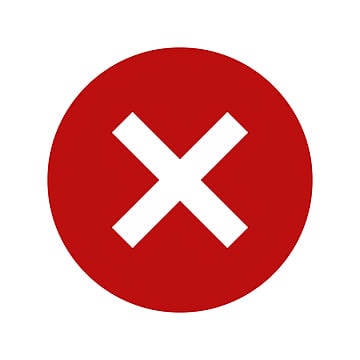和炮友约定的日子
到了跟碧约定的日子,我提前洗澡、刷牙、换上干净衣裳。
碧第二次来的时候,虽然还是长衣长裤,但明显放松多了。我俩像老友那样聊天、讲笑话,基本没有顾忌。
彼此说得来、有共同语言、彼此都不伤害,达成了挺轻松的一种关系。 现在世风日下、到处狗咬狗,能达成这样一种关系,挺舒心。
可我清楚我们不是朋友、也不能成朋友。成了朋友就不好意思再玩儿游戏。 常规揉脚、补水之后,我感叹说:你身体一点没发福。透露一下,怎么保养的?
这是我百试不爽的杀手锏。跟女人聊天,要想抓住女人的心,就必须直击死穴。
她说:什么呀?我这身材都严重走样儿了,现在比怀孕之前还胖十三斤呢,怎么减也减不下去。
十三在佛教里是个好数。我专门请教过。可在咱普通老百姓心里,多少有点不吉祥。
当时这念头一掠而过,我没怎么在意。现在把所有事放在一起,才悟出点名堂,可惜晚了。
她说:我生孩子之前特柳(柳:身材狐媚。);喂奶的时候也还行,起码这儿(指胸)高;现在也不怎么了,该鼓的地方瘪了,不该鼓的地方全出来了。 我把她拉到落地镜子前,仔细打量她:你的胸挺高的呀。
她看着镜子里的映象说:哪里,是奶托高。(奶托:乳罩。)
我说:脱了我看看。
她很自然地解开上衣、脱下、放在椅子上。
我走过去站她身后,解开她乳罩后面的挂钩,把那累赘扔了。她乳罩的确虚高,碗大馒头小。
我把两只手伸到她前面,摸她奶子。可惜啊,脸盘和脚长得挺好,脾气也温和,奶子再大点儿多好。又一想,冥冥之中,可能有个力量在操纵我们所有人,优缺点匀着来,然后花叉着撒到世上,这样才好玩。否则优点集中给一班、缺点都给二班,二班太凄凉了吧?
她问:我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说:常年荒芜、没人开发、欠揉搓。
她说:讨厌,问你正经的呢。
我说:我说的也是正经的啊。知道么,房子只要没人住就毁了,过几年自己能塌。你这还算好呢。我一朋友眼光高,一直不嫁人,结果做了四次大手术,最后一个乳房切了、子宫也摘了,大夫说结个婚就不至于。长时间没人弄就这样,你这是典型内分泌失调。
她说:还真的是,这十多年我家那死鬼就摸过几次。
我说:一摸呢,你就有感觉,分两股,一股冲后脑,一股冲子宫。女人就得被男人弄。弄弄就通了,通了就协调了。真的,就这么简单。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小声说:我体会体会。
看来开始憧憬了。
我观察她的奶子。真的小。太遗憾了。我喜欢大奶子,白花花那种,一肏就乱晃那种。
奶头深褐色,表面有细小皱褶,像干杏脯。
摸第一下,她浑身一震,嘴里发出哆哆嗦嗦的“哈……啊……哼……”像一个字被颤音拖长。那是心尖酥麻的伴唱。
摸第二下,奶头就立起来了。
她说:是不是男人都喜欢大的?
我说:大奶子不敏感,小的更传电。你瞧你奶头多敏感。
她低头看自己的奶头。我轻轻用拇指和中指捻着。
说实话我还是喜欢大白奶。我喜欢老婆奶子的体积。可生活总是充满遗憾。老婆奶头特懒,弄半小时愣不站起来。
她问:她的大?
我继续揉:嗯,有你两个大。
她问:这么说,你老揉搓她?
我说:那是。她毛衣胸口这儿老是黑的,打远处看跟胸毛似的。
她笑了,露出牙龈。笑更刺激了她面部血液循环。她的脸更好看了。
不过她很快收起笑容,可能为自己感到凄凉吧。
停顿一下,她低声说:真羡慕她。可能我老公嫌我这儿小?
我说:越不开发它越小、越小越不开发、恶性循环。
我发现她每颗奶头都出奇的大。此前我弄的最大的,也就曼秀雷敦唇膏那么粗。
碧的奶头绝对超出,倔强挺立。表面细小皱褶几乎都平了,像干杏脯被热水浸泡。
温柔得差不多,该暴力了,否则女的以为你阳痿。男人铺好前戏之后,就需要混横一点儿。
温柔跟混横之间的过渡时机掌握好就可以。
我开始野蛮蹂躏她奶子,同时专心感受她的反应变化。
她面容开始发亮,因为出了薄薄一层细汗,也因为颧骨、脑门、太阳穴、眼睛四周血液循环加速,面皮看上去有了好看的粉红色。
我还站她身后,对她说:俩胳膊抬起来。
她听话地抬起两条胳膊,镜子里她眼光茫然,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
我说:往后、搭我脖子上。
她像驯顺的活体洋娃娃,让干吗干吗。
我俩一起观赏镜子里的美景。一个中年女人,身材不错,光着白白的上身,两条胳膊举起来,攀住身后的流氓。流氓是暗的,四周背景、家具也是重色,隐在暗光里。
我在她耳边低声说:瞧,这女的多好看,站舞台上,台下都是男的,有民工也有罪犯,有当兵的,有老教授,都恶狠狠看你表演。
他们的鸡巴都硬了。
她的脸更红了,开始喘息,像不好受。
我继续捻她奶子,故意拖延进攻步骤。
我喜欢折磨女人,让女人难受,让女人钻心地痒。我爱看女人难受的表情、爱听女人受折磨发出的哼叽。
碧扭过头,仰起脸亲我。开始亲脸,很快亲嘴。她的嘴唇软极了,滚烫,脸也是热热的。
她嘴唇有点儿薄(命苦),但这会儿挺灵活。她不敢伸舌头。这是个时刻想保持体面的屄。
她可能脖子累了,也可能想继续看镜子里的演出,她停止亲吻,头颈恢复原状。胳膊还是高高举起。
我注意到她的胳肢窝里已经出了汗,亮晶晶的。这姿势比较受虐。我喜欢。(四岁看吴琼花被吊绑折磨。)
一般来讲,对着陌生男人亮出胳肢窝会让女人感到屈辱。
为强化她内心的不平衡,我故意没脱衣服。鸡巴硬了,隔着我裤子顶她软屁股。
我一边强力蹂躏她奶子,一边开始亲她脸。她的脸软软的,胳膊还是高高吊我脖子上,不敢下来。良民顺屄。好人。
我闻到她的体味。有淡淡的顶级化妆品余香、有热的汗味,有黏的骚味,有她下边正不断分泌的麝香。混合在一起,怪好闻的。
她的手机忽然炸响。她浑身一哆嗦,回头望着我,好像在征求我的许可。 我说:接呗。你是上帝你做主。
她光着上身跑到玄关、从包包里翻出手机接听。电话内容是关于一笔木材生意。
我走过去,脱了她鞋、袜子、扒了她外裤、内裤。她一边接电话一边轮流抬腿配合我。
脱的过程,我故意不碰她的屄。但我相信,应该湿了。
现在这屄全身赤裸,光脚站我面前打电话,心不在焉、不知所云。
通话完毕,她赶紧挂断电话,后长按一个按键、
我说:往后、搭我脖子上。
她像驯顺的活体洋娃娃,让干吗干吗。
我俩一起观赏镜子里的美景。一个中年女人,身材不错,光着白白的上身,两条胳膊举起来,攀住身后的流氓。流氓是暗的,四周背景、家具也是重色,隐在暗光里。
我在她耳边低声说:瞧,这女的多好看,站舞台上,台下都是男的,有民工也有罪犯,有当兵的,有老教授,都恶狠狠看你表演。
他们的鸡巴都硬了。
她的脸更红了,开始喘息,像不好受。
我继续捻她奶子,故意拖延进攻步骤。
我喜欢折磨女人,让女人难受,让女人钻心地痒。我爱看女人难受的表情、爱听女人受折磨发出的哼叽。
碧扭过头,仰起脸亲我。开始亲脸,很快亲嘴。她的嘴唇软极了,滚烫,脸也是热热的。
她嘴唇有点儿薄(命苦),但这会儿挺灵活。她不敢伸舌头。这是个时刻想保持体面的屄。
她可能脖子累了,也可能想继续看镜子里的演出,她停止亲吻,头颈恢复原状。胳膊还是高高举起。
我注意到她的胳肢窝里已经出了汗,亮晶晶的。这姿势比较受虐。我喜欢。(四岁看吴琼花被吊绑折磨。)
一般来讲,对着陌生男人亮出胳肢窝会让女人感到屈辱。
为强化她内心的不平衡,我故意没脱衣服。鸡巴硬了,隔着我裤子顶她软屁股。
我一边强力蹂躏她奶子,一边开始亲她脸。她的脸软软的,胳膊还是高高吊我脖子上,不敢下来。良民顺屄。好人。
我闻到她的体味。有淡淡的顶级化妆品余香、有热的汗味,有黏的骚味,有她下边正不断分泌的麝香。混合在一起,怪好闻的。
她的手机忽然炸响。她浑身一哆嗦,回头望着我,好像在征求我的许可。 我说:接呗。你是上帝你做主。
她光着上身跑到玄关、从包包里翻出手机接听。电话内容是关于一笔木材生意。
我走过去,脱了她鞋、袜子、扒了她外裤、内裤。她一边接电话一边轮流抬腿配合我。
脱的过程,我故意不碰她的屄。但我相信,应该湿了。
现在这屄全身赤裸,光脚站我面前打电话,心不在焉、不知所云。
通话完毕,她赶紧挂断电话,后长按一个按键、塞进包包。我猜她关机了,不想再被打扰。
被电话一打扰,连惊带吓,她奶头缩回去了,还原成干杏脯。应激缩回是动物界最常见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
我把她揪回大镜子前,还是站在她身后,抱住她,专注凝望镜子里的中年赤裸小怨妇。
她看看镜子里的映象,又低头看看自己,再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摸着两边的骻骨不自信地问:我是不是有点儿胖?
我说:说实话,你够不上胖。
她确实比我老婆瘦。而我老婆也算不上胖,顶多算丰腴。
那碧算什么级别我说不上来,她的奶子尤其让我困惑。
我左手猛力提起她左腿膝弯,右手粗暴扭她脑袋,迫使她脸朝我。她目光慌乱,像误入虎穴的小兔子。
我亲她脸。她的脸肉细腻、绵软,脸面温度略低于接电话之前。
我飞快掏出热鸡巴、戴上套、顶在她阴部那堆热肉里。
龟头独眼,视力不佳,自己找不到洞口。没关系,肉已进锅,慢炖才烂。 我亲她嘴。她的嘴唇在剧烈颤抖,像忽然被鳄鱼啃住的小鹿。
我拱开她的唇,舌尖遭遇她紧紧咬在一起的上下牙,壁垒森严。
我用舌尖在她唇内牙面横着扫过去扫回来。她的牙齿和牙龈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她的口液,清淡无味。
我强攻不下,立刻迂回改道,扳她脸的右手顺她下巴、脖子往下,再次肆虐奶子。
她的奶头再次亢奋昂扬,这回更加舒展不屈,像刘胡兰一样挺立。我本能想低头舔嘬刘胡兰,可惜够不着(我一米八五)。
我一边亲她一边右手瞎闯,混蛋一样盖住她的毛毛,故意打破章法,轻一下重两下胡揪乱扯,像窑子里的民工。
大镜子前,她左腿一直被我抬着、屄屄口一直被我顶着。我没费劲就摸到她豆豆。那颗豆大小正常,倒不像奶头那么夸张。
我右手摸她屄口。她浑身一哆嗦,我的嘴唇舌头立刻感觉她的上下牙松开了一道缝。
我把舌头顶进去,感觉到她的舌头软绵绵往后躲,像掌柜的闺女瞅见日寇。 我的牙撞到她的牙。我的舌头试图逮住那掌柜的闺女。
镜子里,她的左腿被我强力撩起,我紫红色小脑袋抵住她的屄。
我右手摸她屄。她的屄口果然不怎么湿润。功能退化,欠练。
我把她的手按她自己豆豆上。她那手快速逃离。我再揪过来。她难为情地自己揉豆豆。
我的硬鸡巴开始发力往里顶。入洞颇费了些力。一个是因为都站着、角度不好掌握,再有就是她确实紧。
扳她左腿让她光脚踹镜子上,我腾出左手,跟右手合龙,扒开她的肉屄。 我动作很粗野,把她粉嫩的屄肉都翻出来了。(inside-out) 我喘着气,鸡巴发狠。终于艰难进洞。屄肉被鸡巴连带肏进洞。(outside-in)
她的鼻子在辛苦换气,换气量不够,忽然嘴里唿出一大口气,一点儿没糟踏全喷我嘴里。我的脸蛋子鼓起来。
她唿出的是废气,我自然不会再循环。我赶紧松点儿口,吐出废气。她趁机发出一声“哎哟”,听上去很色情。
金箍棒入洞到位,凝住不动,先扎稳阵脚。
我看着她踹在镜子上的那只光脚。那脚真养眼,光顺柔滑,脚趾白净、趾甲透亮,我的鼻腔立刻出现上次揉她脚的时候闻见的那股若有若无的独特香臭。 她的光脚一定是在紧张和激动刺激下出了汗,因为我看见那脚踩镜子的接触面四周出现几毫米的淡出水雾。
镜子前,她叉着大腿、被迫揉着自己的阴蒂。我两手大力掰开她屄肉,刚硬的鸡巴在她热屄里开始缓慢擦动。
左三下、右三下。慢慢地,滑膛炮内部被擦出保养油脂。
她可能不好意思再看镜子,所以扭过脸来亲我。我甩开,让她看镜子。 其实我犯了大忌。肏屄照镜子能招鬼。不过这是后话,等我知道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
我不着急大动,而是稳住下盘,控制节奏,腰部以几乎看不出的幅度缓缓移动。
此时,她的脸已经通红了,滑膛炮内膛更加浸润。我能感觉出来,因为出出进进越来越顺滑。
我双手攥住她屁股两边,微微摇晃她的身体,而我的身体静止不动,以逸待劳。
这会儿要是有眼神儿不好的从对面楼拿望远镜瞧见我,准以为瞧见柳下惠了呢。
她可能忽然想起我的建议,这时抬起左胳膊往后扬起、揽住我的头。
嵴柱右侧弯、右手更加往下、不但摸着她自己的屄口、也摸到我的鸡巴。 这个细节怎么这么熟悉?在哪儿见过?一时想不起来。
事后我回味的时候才想起来,这细节我在此前的梦里梦见过。
她的手绵软、温凉,摸得我很受用。鸡巴受到额外刺激,有点儿想哗变。 我意识到鸡巴挺动的开始加大加快,赶紧咬牙抢档减速。她略微不满,摇胯紧追。
我一边滑膛一边揉奶一边欣赏镜子里的画面。
镜子里,这四十多岁的屄高高扬起左胳膊缠住我的头、光着身子红着脸抬着腿扭着胯用屄贪婪嘬鸡巴。
暗影里,柳下惠穿戴整齐道貌岸然铁着脸捏着奶暗暗撞钟。
女人的淫水越来越多了,在牛顿发现的法则下,往下流、往下流,积少成多汇集到我蛋蛋上,黏黏的,不舒服。
柳下惠的撞钟频率逐渐加快,到一秒一次又慢下来,不能再快,力争维持这个水平撞够一个钟。
耳边的喘息加剧了。镜子里,女人的腰开始大力扭动,像母狗发春,像上了岸的海豚。
要发生什么太明显不过。我还没提速,她的大腿肌群突然开始啪啪抖动。 母狗挺直成木头人、浑身僵硬、不唿不吸、维持六、七秒才漏出叹息、木头人开始松软,成了布娃娃。
一时间,布娃娃脸色煞白,手冰凉,要瘫痪。
柳下惠腹股沟里面开始隐隐作痛。精子开始暴动,精液开始沸腾。监仓内的局面有点儿要失控。
前列腺助纣为虐、开始点火施压。脆弱的输精管不堪重负,开始哆嗦。 只有典狱长孤身寡人声嘶力竭喊叫着:不许出去。
精子都是混蛋,哪朝哪代听过人话?
输油管后面火势凶猛。强大的气体压着一股先行部队嗖地飙出。
一精既出、驷马难追。后面的精液亡命逃窜,嚎叫着、欢唿着,争先恐后奔出狭窄的油管隧道。乌拉。
典狱长颓然摇晃,有点儿站不住,从镜子里看到一张扭曲可憎的脸。
女人用手掌给典狱长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典狱长说:没守住。
女人微笑说:已经很好了。真的,我从结婚就没这么舒坦过。作女人原来这么美,比网上她们说得还好。
典狱长问:什么感觉?
她说:腿软、心跳。你呢?
典狱长说:头发根都软了。
她说:你刚才吼,真好听。我爱听。
我说:如果可以,希望能听到你叫唤。叫唤是自我解放的关键步骤。不敢叫唤的女人,一定是被压抑被扭曲的。
她说:好吧,下次我试试。我说,你射得可真凶。你总射这么多吗?
我问:看心情吧。
女人都是骚狐狸。女人们在街头室内菜场田间走来走去,做各种表情说各种话,归根结底都夹着一块骚屄。
羊子啃秃一片坡,自然会啃其它有草的坡。
眷养女人,切记营养均衡。她缺什么她肚子里门儿清;一出去恶补,你就绿帽男了。
*** *** *** ***
我问:你不洗洗?
她说:哦不了。头发湿了麻烦,得等干、还得重新梳。
我说:好办,我有辙。跟我来。
我带她走进卫生间,让她光着脚屁股朝外蹲在白瓷马桶边沿儿上。
我打量她的光后背、白屁股。女人这个姿势曲线毕露,在我看来格外色情。 我拿起花洒,用温水给她冲两瓣屁股中间的地方。
她自己伸手洗。我把手伸到下面帮她洗。她浑身一紧。
我一边揉洗一边贴她耳边说:放松。享受过男人给你洗屄么?
她摇头说:没。想都没想过。
我轻轻搓她豆豆揉她屄,说:你下边儿滑熘熘、软乎乎,手感不错。你舒服么?
她点头说:嗯,真舒服,挺刺激的。
我开始洗她屁眼儿,轻轻按揉、轻轻搓。
她发出:喔!啊、别、脏。
我亲她光膀子,从容说:不脏,你什么都不脏。喜欢被我这么洗么?
她点头说:嗯,喜欢。
我问:什么感觉?
她说:怪怪的。你给别的女人这么洗过么?
我说:没。
她问:那为什么给我洗?
我说:没为什么。就是想。
沉默。水声。默默享受。哗哗的水声。
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她叹口气说:你这么洗下去,永远洗不干净啊。
我当然明白她什么意思。我的手指很敏感的,能在清水中分辨出黏滑体液。我知道她又分泌了。
我对她耳语说:想尿的话可以尿。
她说: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尿了,尿你手上了。
这我倒真没感觉出来,因为花洒喷出的水温和她的尿也许接近。
我说:下回我准备两个空啤酒扎。(扎:jar,玻璃制品。)
她微笑说:还两个?我可尿不了那么多。
我说:咱俩一人一个,比赛。
她又笑。那笑容甜甜的。
*** *** *** ***
从卫生间出来、擦干。
尘埃落定、气喘平息,各自穿戴整齐,正襟危坐,都正人君子似的。
我再次细细看她。脸上红晕还在。比起第一次见面,精神好多了。
她看我看她,赶紧低垂眼皮,有点儿不好意思。
她问:你真有什么救急偏方?
我说:当然。
她说:能告诉我么?
我说:我不能这么告诉你。
她说:怎么这样?还卖关子?
我说:拜托,你还有点儿传统美德么?求方子就你这样?真没规矩。
她笑了,说:好吧,我请你吃饭,馆子任你挑,行不行?
我说:这还算有点儿诚意。不过今天不行。
她问:怎么?忙?后面还有约会?
我说:不,只是……
她拉着我的胳膊说:是什么?没关系。告诉姐姐。
我说:是我私人的事儿。
她说:我都告诉你那么多关于我的事儿了,你干吗把自己包得这么紧?你怕什么?怕我缠上你?
我说:我有很多事。我不是普通男人。我根本就不是人。
她噗嗤笑了,说:好吧。我能再给你打电话么?
我说:成。
她望着我,轻声说:谢谢你。我一直看小电视,今天看了宽银幕。
我明白她什么意思。我拓宽了她的眼界、让她体验到了快乐。可我承受得起这感激么?我给打开的不是潘多拉盒么?
最幸福的奴隶意识不到自己身为奴隶。最痛苦的奴隶是能够意识到自己身为奴隶、不甘于终身为奴、却找不到“转正”途径。
世态炎凉,只剩下借火的陌生人之间的温暖。她呢?到我这儿借了个火儿。 我点了她,点了她渴望已久的、早该烧的火。
可是我点的火正在燎原、正在失控。我是纵火犯。我有罪。我到底是恩人还是罪犯?
千言万语,经过浓缩提炼,出口成了淡淡四个字:别这么说。
她站玄关,忽然抱住我,不动、也不再说话。
我和她一起静静享受这几秒钟的温暖。
我闻她肉体溢出的麝香。